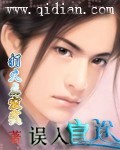新星小说>盛世女侯完整版全文免费 > 第401章从此有人替她护航(第1页)
第401章从此有人替她护航(第1页)
与季将军的军队碰面之后,言蹊自然便了解了所有了。听说慧安县主被呼延炅所擒,他便自己带队去寻了。这才……有了之后的事。
至于言歌,是他在来泰城的路上碰到的。龄龄则是随苏爷爷一起出来的,后听说他要来琅琊关也随上了他。
言蹊无意泄露时非晚的秘密。不过龄龄出门时是随苏爷爷一起的,苏爷爷对龄龄是全然信任不会生出半分顾虑的,因此无需自己多言龄龄其实便已知了。龄龄知,为解言歌心结,言歌自然也知。
不过他们之间能相议此事,都不是因他们是长嘴之人,只因他们之间对于彼此,都是百分百的全然信任。
“我是从苏爷爷那知道的。”似担心时非晚怪责言蹊,龄龄立马说道:“是我同言歌多叨了几句。不过我们绝不会乱说的,死都不会的。”
时非晚听她提起此乃苏爷爷相告,便也估着眼前三人定是相当可信之人,加之对自己身份败露的事她也已有心理准备,便道:“无防。只是,祖父身体好了么?”
言蹊方才叙述了一翻他来此的经历,时非晚没有忽略他方才提起苏爷爷接手漠州主力的事。
言蹊听时非晚唤了一声“祖父”,连“外”字都给省了,心中不免一触,忙道:“自然未有多好,不过郎中说苏爷爷乃是心病,郁结已散,再养养会好起来的。苏爷爷以前就有此郁,多年累积,听你出事更是差点呛过气去。如今知你好着,往年心结也可解,若不是军务缠身,好好休养一阵当不会有性命之忧了。只可惜泰城一破,这担子又大了。”
言蹊说着说着便觉自己说得不大妥帖,忙又抬头道:“姑娘不必担心,苏爷爷他没事,只是忧虑于你。因此也遣了我来,托我送给姑娘几句话。”
时非晚一听苏老将军有话带给自己,立马问道:“且说。”
“苏爷爷说,他戎马半生,所见最多便是死亡。看多了生死,看惯了生死,便已知:生死面前,世俗规矩不过是庸人自扰,声名荣辱不过是虚妄浮云,倒不如肆意而活,交几个真心人,做几件潇洒事,临死之时,有所忆之事,有所念之人,于天无愧,于己无憾,便足矣。
故,姑娘所行,是荣是辱,苏家无意干预。会忧会虑,不过是怕姑娘前路艰苦,步履难行。苏爷爷今生之憾,便是还未能瞧见姑娘得幸。因此,姑娘若退,无论受了何等委屈,苏家定当倾囊相护,三代基业百年军功为姑娘换一个公道也在所不惜。
姑娘若进,世俗若又难容此行,那么,漠州十万边军,四十万百姓,必当为姑娘护航,风雨共行!”
言蹊话止之时,时非晚怔怔的呆在了原地。
许十来年的记忆里,素来乃是一人而行,从不知家族倚仗乃为何物,过去之不幸也都来源于那些所谓的家人,现代的记忆里也是孤儿之身,时非晚一时之间,竟不信此言之真实来。只心湖此瞬间似被什么狠狠砸中,湖底有什么坚硬的东西似蓦地被化了开,平静被扰,一汪激浪开始剧烈沉浮而起,久久已难宁神……